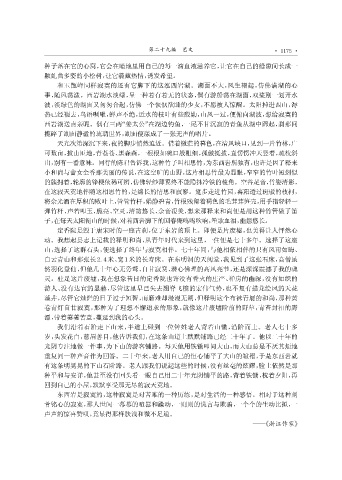Page 1237 - 莲都区志
P. 1237
第二十九编 艺文 · 1175 ·
种子落在它的心窝,它会在暗地里用自己的每一滴血液滋养它,让它在自己的缝隙间长成一
颗虬曲多姿的小松树,让它潜藏热情,诱发希望。
和玉甑峰同样寂寞的还有它脚下的这泓西岩湖。湖面不大,风生褶起,仿佛满湖的心
事,随风荡漾。西岩湖水淡绿,呈一种若有若无的状态,偶有游船荡在湖面,双桨刚一划开水
波,淡绿色的湖面又匆匆合起,仿佛一个恹恹欲睡的少女,不愿被人惊醒。太阳掉进西山,溽
热已经褪去,鸟语啁啾,蝉声不绝,近水的枝叶有些殷勤,山风一过,便俯向湖波,想给寂寞的
西岩湖送点亲昵。偶有三两“姜太公”在湖边钓鱼,一尾不甘沉寂的青鱼从湖中蹿起,刹那间
揽碎了湖面静谧的琉璃世界,湖面便漾成了一张无声的唱片。
天光次第深沉下来,夜的脚步悄然迫近。借着微茫的暮色,在清风峡口,见到一片竹林,广
可数亩,披山匝地,青苍苍、黑森森,一根根如碗口般粗细,孤傲挺拔,直愣愣冲天竖着,疏枝斜
出,别有一番意味。同行的陈君告诉我,这种竹子叫相思竹,为东西岩所独有,也许是因了释来
小和尚与畲女全香那美丽的传说,在这空旷的山野,这片相思竹最为显眼,窄窄的竹叶短剑似
的簇拥着,轮廓的铮梗依稀可辨,仿佛轻纱薄翼终不能隐抹冷铁的棱角。空谷足音,竹姿清影,
在这寂天寞地伴随这相思竹的,是绵长的情思和寂寥。踅步走进竹园,暮阳透过斑驳的枝柯,
将余光洒在厚积的败叶上,管管竹杆,娟静碧青,竹根残留着褐色的毛茸茸笋壳,用手指轻轻一
弹竹杆,声若叩玉,脆亮、空灵,清韵悠长、余音凄美,想来那释来和尚便是用这种竹管做了笛
子,在每天太阳衔山的时候,对着西岩脚下的回春庵呜呜吹响,笙歌血泪,幽怨悠长。
定香院是毁于唐宋时的一座古刹,位于东岩的顶上。即便是片废墟,也美得让人怦然心
动。我想起县志上记载的释明和尚,从青年时代来到这里,一住便是七十多年。选择了这座
山,选择了这群石头,便选择了终年与寂寞相伴。七十年间,与他相依相伴的只有风雨如晦、
白云青山和那张长2.4米、宽1米的长寿床。在东明洞的天阅堂,我见到了这张石床,高僧虽
然羽化登仙,但他几十年心无旁骛、自甘寂寞、潜心佛理的高风亮节,还是深深震撼了我的魂
灵。驻足这片废墟,我在想象昔日的定香院也许没有香火的庄严、禅房的幽深,没有如织的
游人、没有达官的显赫,尽管这里早已失去翘脊飞檐的宏伟气势,也不复有描龙绘凤的天花
藻井,尽管它灿烂的日子过于短暂,而磨难却漫漫无期,但释明这个布袜青屣的和尚,那种黄
卷青灯自甘寂寞,那种为了理想不懈追求的形象,就像这片废墟阶前的野草,青苔封扣的野
潭,带着萋萋苦意,蔓延到我的心头。
我们沿着石阶走下山来,半道上碰到一位钟姓老人背着山锄,沿阶而上。老人七十多
岁,头发花白,慈眉善目,他告诉我们,在这条山道上默默铺路已经二十年了。他以二十年的
光阴专注地做一件事,为下山的游客铺路。每天他用铁锄叩问大山,而大山总是不厌其烦地
重复同一种声音作为回答。二十年来,老人用自己的恒心铺平了大山的皱褶,于是东西岩就
有这条明晃晃的下山石阶路。老人跟我们说起这些的时候,没有丝毫的炫耀,脸上依然是那
种平和与安详,他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自己用二十年光阴铺平的路,背着铁锄,枕着夕阳,再
回到自己的小屋,默默享受那无尽的寂天寞地。
东西岩是寂寞的,这种寂寞是对苦难的一种历练,是对生活的一种感悟。相对于这种刻
骨铭心的寂寞,那人世间一幕幕的喧嚣和躁动,一则则的谎言与欺骗,一个个的生动比拟,一
声声的惊喜赞叹,竟显得那样肤浅和微不足道。
——《浙江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