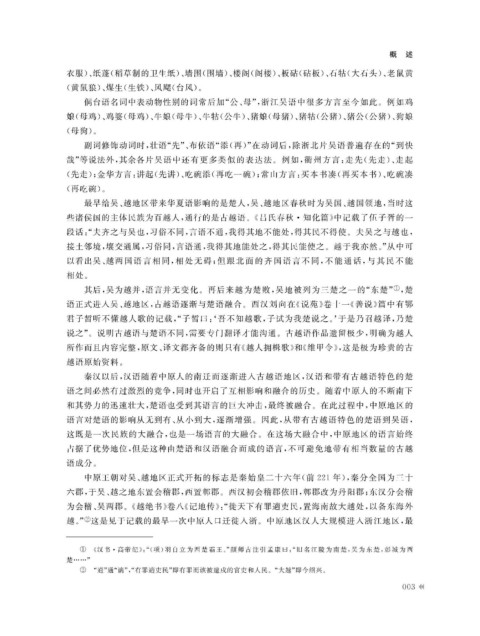Page 26 - 方言志
P. 26
衣服)、纸蓬(稻草制的卫生纸)、墙围(围墙)、楼阁(阁楼)、板砧(砧板)、石牯(大石头)、老鼠黄
(黄鼠狼)、煤生(生铁)、风飔(台风)。
侗台语名词中表动物性别的词常后加“公、母”,浙江吴语中很多方言至今如此。例如鸡
娘(母鸡)、鸡婆(母鸡)、牛娘(母牛)、牛牯(公牛)、猪娘(母猪)、猪牯(公猪)、猪公(公猪)、狗娘
(母狗)。
副词修饰动词时,壮语“先”、布依语“添(再)”在动词后,除浙北片吴语普遍存在的“到快
哉”等说法外,其余各片吴语中还有更多类似的表达法。例如,衢州方言:走先(先走)、走起
(先走);金华方言:讲起(先讲)、吃碗添(再吃一碗);常山方言:买本书凑(再买本书)、吃碗凑
(再吃碗)。
最早给吴、越地区带来华夏语影响的是楚人,吴、越地区春秋时为吴国、越国领地,当时这
些诸侯国的主体民族为百越人,通行的是古越语。《吕氏春秋· 知化篇》中记载了伍子胥的一
段话:“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得使。夫吴之与越也,
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从中可
以看出吴、越两国语言相同,相处无碍;但跟北面的齐国语言不同,不能通话,与其民不能
相处。
其后,吴为越并,语言并无变化。再后来越为楚败,吴地被列为三楚之一的“东楚”① ,楚
语正式进入吴、越地区,古越语逐渐与楚语融合。西汉刘向在《说苑》卷十一《善说》篇中有鄂
君子皙听不懂越人歌的记载,“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于是乃召越译,乃楚
说之”。说明古越语与楚语不同,需要专门翻译才能沟通。古越语作品遗留极少,明确为越人
所作而且内容完整,原文、译文都齐备的则只有《越人拥楫歌》和《维甲令》,这是极为珍贵的古
越语原始资料。
秦汉以后,汉语随着中原人的南迁而逐渐进入古越语地区,汉语和带有古越语特色的楚
语之间必然有过激烈的竞争,同时也开启了互相影响和融合的历史。随着中原人的不断南下
和其势力的迅速壮大,楚语也受到其语言的巨大冲击,最终被融合。在此过程中,中原地区的
语言对楚语的影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增强。因此,从带有古越语特色的楚语到吴语,
这既是一次民族的大融合,也是一场语言的大融合。在这场大融合中,中原地区的语言始终
占据了优势地位,但是这种由楚语和汉语融合而成的语言,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当数量的古越
语成分。
中原王朝对吴、越地区正式开拓的标志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 年),秦分全国为三十
六郡,于吴、越之地东置会稽郡,西置鄣郡。西汉初会稽郡依旧,鄣郡改为丹阳郡;东汉分会稽
为会稽、吴两郡。《越绝书》卷八《记地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
越。”② 这是见于记载的最早一次中原人口迁徙入浙。中原地区汉人大规模进入浙江地区,最
① 《汉书·高帝纪》:“(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颜师古注引孟康曰:“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
楚……”
② “適”通“谪”,“有罪適吏民”即有罪而该被遣戍的官吏和人民。“大越”即今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