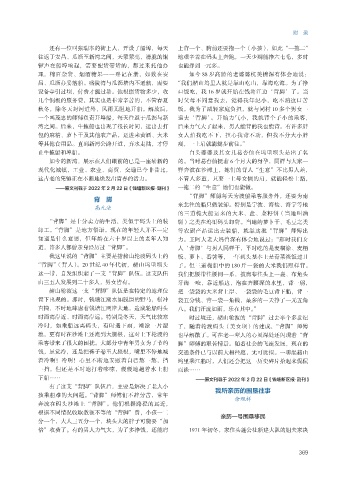Page 433 - 钱塘年鉴(2022)
P. 433
附 录
还有一位叫张瑞本的街上人,开设了船埠,每天 上背一个、胸前还要抱一个(小孩),如此“一拖二”
往返于安昌、瓜沥至新湾之间,天蒙蒙亮,清脆的铜 地艰辛着在码头上奔跑,一天少则能挣六七毛,多时
锣声在船埠响起,需要配货带货的,都过来托他办 也能挣到一元多。
理,棉百杂货、烟酒糖果一一登记在册,如数在安 如今 88 岁高龄的老婆婆杭美锦深有体会地说:
昌、瓜沥办妥落船。盛陵湾与瓜沥塘内不通航,需要 “我们赭山坞里人就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为了挣
设备牵引过坝,付费才能过塘。他根据货物多少,收 口饭吃,我 16 岁就开始在钱塘江边‘背脚’了。当
几个铜板的服务费,其实也是非常辛苦的,不管春夏 时父母不同意我去,觉得我年纪小,吃不消这口苦
秋冬,除冬天封河道外,风雨无阻地开船。解放后, 饭。我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就与同村 10 多个男女一
一个叫茂忠的师傅负责开埠船,每天往返于瓜沥与新 道去‘背脚’。开始力气小,我就背个子小的乘客,
湾之间。后来,牛拖船也出现了很长时间,运出去打 后来力气大了起来,男人能背的我也能背。有许多胖
包的麻精、萝卜干及其他农产品,运进来黄酒、大米 女人怕我吃不下,担心我背不动,但我不分大小胖
等其他食用品。直到新湾公路开道,弃水走陆,才停 瘦,一上肩就能健步前往。”
止牛拖船和埠船。 白头婆婆及其女儿葛杏仙在坞里坝头是出了名
如今的新湾,展示在人们眼前的已是一座崭新的 的。当时葛杏仙挺着 6 个月大的身孕,同样与大家一
现代化城镇,工业、农业、商贸、交通已今非昔比, 样奔波在沙滩上,她们的背人“生意”不比男人差,
这古老的集镇正在不断地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不管人多重,只要一上母女俩的肩,就能轻松上路,
—原文刊载于 2022 年 2 月 22 日《钱塘新区报·副刊》 一拖二的“生意”她们也能做。
“背脚”师傅每天为渡船乘客服务外,还要为南
背 脚
来北往的船只做装卸。特别是宁波、海盐、海宁等地
高元法
的三道桅大船运来的大米、盐、菜籽饼(当地叫油
“背脚”是十分卖力的生活,类似于码头上的装 饼)之类在坞里码头卸货。当地的萝卜干、毛豆之类
卸工。“背脚”是地方俗语。现在的年轻人并不一定 等农副产品运出去装船,就靠这批“背脚”师傅出
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年龄在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知 力。王阿大老大妈曾深有体会地说过;“那时我们女
道,许多人都曾亲身经历过“背脚”。 人‘背脚’与男人同样干,平时吃的是麦糊涂、麦粞
我这里说的“背脚”主要是指赭山轮渡码头上的 饭、萝卜、番薯等,一年到头基本上是青菜淡饭过日
“背脚”(背人)。20 世纪 40 年代初,赭山坞里坝头 子。但三道桅船中的 180 斤一袋的大米我们照样背。
这一带,自发组织起了一支“背脚”队伍。这支队伍 我们把腰带往腰间一系,披肩布往头上一裹、布角头
由三五人发展到二十多人,男女皆有。 牙齿一咬,靠近船边,泡在齐腰深的水里,背一躬,
赭山轮渡这一支“背脚”队伍是在特定的地理位 把一袋袋的大米背上岸、一袋袋的毛豆背下船,背一
置下出现的。那时,钱塘江潮水如脱缰的野马,横冲 袋五分钱、背一袋一角钱,最多的一天挣了一元五角
直撞,不时地肆虐着钱塘江两岸大地,造成轮船码头 八。我们汗流如雨,乐在其中。”
时而离岸近、时而离岸远。特别是冬天,天气比较寒 时过境迁,赭山轮渡的“背脚”过去半个多世纪
冷时,如乘船远离码头,有时遇下雨,滩涂一片湿 了,随着轮渡码头(美女坝)的建成,“背脚”师傅
漉,更有时在沙滩上还淹到大腿根,这对上下轮渡的 也早解散了。可在老一辈人的心灵深处还闪现着“背
乘客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大部分中青年男女为了节约 脚”师傅的艰苦情景。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现在的
钱,虽觉冷,还是把裤子卷至大腿根,嘴里不停地喊 交通条件已与以前大相径庭,无可比拟。一聊起赭山
着冷啊!冷啊!心里不断地安慰着自己熬一熬,挡 坞里乘江船时,人们还会把这一历史碎片拾起来侃侃
一挡,但还是不时地打着哆嗦,慢慢地趟着水上船 而谈……
下船…… —原文刊载于 2022 年 2 月 22 日《钱塘新区报·副刊》
有了这支“背脚”队伍后,主要是解决了老人小
我所亲历的围垦往事
孩乘船难的大问题。“背脚”师傅们不辞劳苦,常年
余观祥
奔波在码头沙滩上“背脚”。他们根据路程的远近,
根据不同情况收取数额不等的“背脚”费,小孩一二
亲历一号围垦移民
分一个,大人三五分一个,块头大的胖子可能要“加
倍”收费了。有的男人力气大,为了多挣钱,还能肩 1971 年初冬,家住头蓬公社新建大队的姐夫家决
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