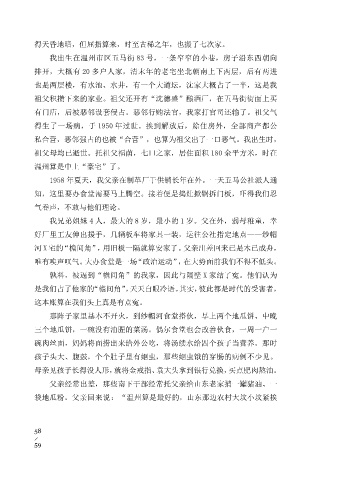Page 66 - 《鹿城史志》二O二二·秋冬(总第十八期)
P. 66
得天昏地暗,但屈指算来,时至古稀之年,也搬了七次家。
我出生在温州市区五马街 83 号,一条窄窄的小巷,房子沿东西朝向
排开,大概有 20 多户人家,清末年的老宅坐北朝南上下两层,后有两进
也是两层楼,有水池、水井,有一个大道坛,沈家大概占了一半,这是我
祖父积攒下来的家业。祖父还开有“沈德盛”酿酒厂,在五马街街面上买
有门店,后被恶邻设套侵占。恶邻行贿法官,我家打官司还输了。祖父气
得生了一场病,于 1950 年过世。挨到解放后,除住房外,全部商产都公
私合营,恶邻强占的也被“合营”,也算为祖父出了一口恶气。我出生时,
祖父母均已逝世。托祖父福荫,七口之家,居住面积 180 余平方米,时在
温州算是中上“豪宅”了。
1958 年夏天,我父亲在制革厂干供销长年在外。一天五马公社派人通
知,这里要办食堂需要马上腾空。接着便是捣灶掀锅拆门板,吓得我们忍
气吞声,不敢与他们理论。
我兄弟姐妹 4 人,最大的 8 岁,最小的 1 岁。父在外,弱母稚童,幸
好厂里工友伸出援手,几辆板车将家具一装,运往公社指定地点——纱帽
河 X 宅的“檐间角”,用旧板一隔就算安家了。父亲出差回来已是木已成舟,
唯有唉声叹气。大办食堂是一场“政治运动”,在大势面前我们不得不低头。
孰料,被逼到“檐间角”的我家,因此与隔壁 X 家结了寃。他们认为
是我们占了他家的“檐间角”,天天白眼冷语。其实,彼此都是时代的受害者,
这本账算在我们头上真是有点寃。
那阵子家里基本不开火,到纱帽河食堂搭伙,早上两个地瓜饼、中晚
三个地瓜饼,一碗没有油腥的菜汤。偶尔食堂也会改善伙食,一周一户一
碗肉丝面,妈妈将面捞出来给外公吃,将汤续水给四个孩子当营养。那时
孩子头大、腹鼓,个个肚子里有蛔虫,那些蛔虫饿的穿肠的病例不少见。
母亲见孩子长得没人形,就将金戒指、袁大头拿到银行兑换,买点肥肉熬油。
父亲经常出差,那些南下干部经常托父亲给山东老家捎一罐猪油、一
袋地瓜粉。父亲回来说:“温州算是最好的,山东那边农村大坟小坟紧挨
58
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