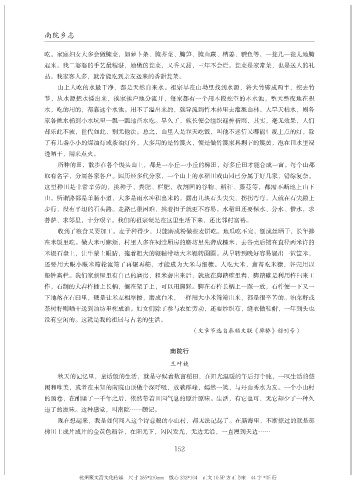Page 177 - 南院乡志
P. 177
南院乡志
吃。家庭妇女大多会做腌菜,如萝卜条、腌芥菜、腌笋、腌山蕨、糟姜、糟鱼等,一瓮儿一瓮儿地腌
起来。我二婆婆的手艺最精湛,她做的瓮菜,又香又甜,三年不会烂。瓮菜是家常菜,也是送人的礼
品。我家客人多,就常能吃到亲友送来的香甜瓮菜。
山上人吃的水最干净,都是天然自来水。祖宗早在山坳里找到水源,将大竹劈成两半,挖去竹
节,从水源把水播出来,挨家挨户地分流开,每家都有一个用木段挖空的木水池,整天整夜地在积
水,吃的用的,都靠这个水池。用不了溢出来的,就导流到竹木林里去灌溉山林。大旱天枯水,则各
家各挑水桶到小水坑里一瓢一瓢地舀水吃。旱久了,族长便会组织迎神祈雨,其实,毫无效果,人们
却乐此不疲,世代如此,别无他法。总之,山里人是靠天吃饭,叫他不迷信又哪能!晚上点的灯,除
了有几盏小小的煤油灯或茶油灯外,大多用的是竹篾火,便是做竹篾家具剩下的篾黄,泡在田水里浸
透晒干,用来点火。
所种的田,散步在各个馒头山上,都是一小丘一小丘的梯田,好多丘田才能合成一亩。每个山都
取有名字,分属各家各户。因历经多代分家,一个山上的水稻田或山园已分属于好几家,错综复杂。
这里种田是非常辛劳的,挑种子、粪肥、栏肥,收割回的谷物、稻秆、藤蔓等,都需不断地上山下
山。所谓路都是羊肠小道,大多是雨水冲积出来的,露出几块石头尖尖、拐拐弯弯,人就在石尖隙上
步行,没有平坦的石头路。走路已很困难,挑着担子就更不容易。水稻田还要保水、分水、借水,求
菩萨、求邻里,十分艰辛。我们的祖宗硬是在这里生活下来,还比邻村富裕。
收到了粮食又要加工。麦子种得少,只能磨成粉做些麦饼吃。地瓜吃不完,刨成丝晒干,长年掺
在米饭里吃。做大米可麻烦,村里人多在祠堂厢房的磨坊里先砻成糙米,去谷壳后铺在直径两米许的
米辗石盘上,让牛蒙上眼睛,拖着粗大的辗轴带动大米辗转圈圈。从早转到晚好容易辗出一笸筐米,
还要用大眼小眼米筛轮流筛了再辗再筛,才能成为大米与细糠。人吃大米,禽畜吃米糠,谷壳用以
垫牲畜栏。我们家新屋里有自己的磨房,粗米砻出来后,就放在脚踏碓里舂,脚踏碓是利用杵臼来工
作,石制的大舂杵插上长柄,搁在架子上,可以用脚踩。脚在石杵长柄上一踩一放,石杵便一下又一
下地落在石臼里,硬是让米互相摩擦,磨成白米,一样用大小米筛筛出来,都是很辛苦的。油菜籽或
茶树籽则晒干送到油坊里榨成油。妇女们除了参与农忙劳动,还要纱织布,缝衣做鞋帽,一年到头也
没有空闲的。这就是我的祖居与古老的生活。
(文章节选自泰顺文联《廊桥》创刊号)
南院行
王叶婕
秋天的记忆里,童话般的生活,就是守候着数亩稻田,在阳光温暖的午后打个盹,一叹生活的悠
闲和唯美,或者在未知的南院山顶做个深呼吸,放歌群峰,嫣然一笑,与丹山秀水为友。一个小山村
的画卷,在酣睡了一千年之后,依然带着田园气息的原汁原味。生活,有它也可,无它却少了一种久
违了的滋味。这种感觉,叫南院……题记。
现在想起来,我是如何闯入这个诗意般的小山村,都无法记起了。在脑海里,不断掠过的就是那
梯田上成片成片的金黄色稻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无边无沿,一直漫到天边……
152
杭州聚文斋文化传媒 尺寸 285*210mm 版心 232*164 正文 10.5P 方正书宋 44 字 *35 行 杭州聚文斋文化传媒 尺寸 285*210mm 版心 232*164 正文 10.5P 方正书宋 44 字 *35 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