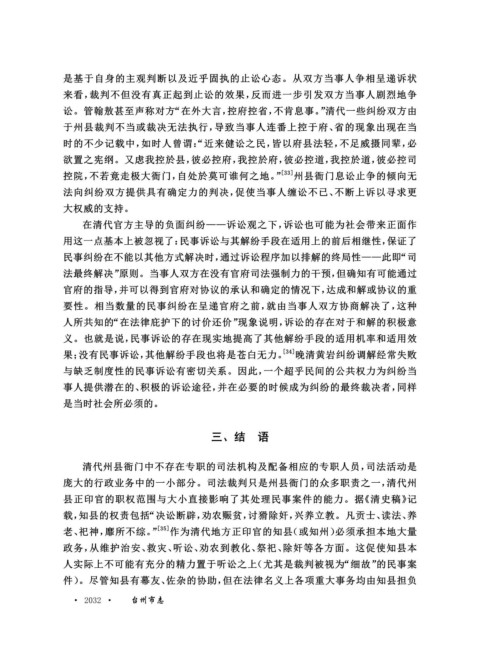Page 976 - 《台州市志》下册
P. 976
是基于自身的主观判断以及近乎固执的止讼心态。从双方当事人争相呈递诉状
来看,裁判不但没有真正起到止讼的效果,反而进一步引发双方当事人剧烈地争
讼。管翰敖甚至声称对方“在外大言,控府控省,不肯息事。”清代一些纠纷双方由
于州县裁判不当或裁决无法执行,导致当事人连番上控于府、省的现象出现在当
时的不少记载中,如时人曾谓:“近来健讼之民,皆以府县法轻,不足威摄同辈,必
欲置之宪纲。又虑我控於县,彼必控府,我控於府,彼必控道,我控於道,彼必控司
[33]
控院,不若竟走极大衙门,自处於莫可谁何之地。” 州县衙门息讼止争的倾向无
法向纠纷双方提供具有确定力的判决,促使当事人缠讼不已、不断上诉以寻求更
大权威的支持。
在清代官方主导的负面纠纷——诉讼观之下,诉讼也可能为社会带来正面作
用这一点基本上被忽视了:民事诉讼与其解纷手段在适用上的前后相继性,保证了
民事纠纷在不能以其他方式解决时,通过诉讼程序加以排解的终局性——此即“司
法最终解决”原则。当事人双方在没有官府司法强制力的干预,但确知有可能通过
官府的指导,并可以得到官府对协议的承认和确定的情况下,达成和解或协议的重
要性。相当数量的民事纠纷在呈递官府之前,就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了,这种
人所共知的“在法律庇护下的讨价还价”现象说明,诉讼的存在对于和解的积极意
义。也就是说,民事诉讼的存在现实地提高了其他解纷手段的适用机率和适用效
[34]
果;没有民事诉讼,其他解纷手段也将是苍白无力。 晚清黄岩纠纷调解经常失败
与缺乏制度性的民事诉讼有密切关系。因此,一个超乎民间的公共权力为纠纷当
事人提供潜在的、积极的诉讼途径,并在必要的时候成为纠纷的最终裁决者,同样
是当时社会所必须的。
三、结 语
清代州县衙门中不存在专职的司法机构及配备相应的专职人员,司法活动是
庞大的行政业务中的一小部分。司法裁判只是州县衙门的众多职责之一,清代州
县正印官的职权范围与大小直接影响了其处理民事案件的能力。据《清史稿》记
载,知县的权责包括“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
[35]
老、祀神,靡所不综。” 作为清代地方正印官的知县(或知州)必须承担本地大量
政务,从维护治安、救灾、听讼、劝农到教化、祭祀、除奸等各方面。这促使知县本
人实际上不可能有充分的精力置于听讼之上(尤其是裁判被视为“细故”的民事案
件)。尽管知县有幕友、佐杂的协助,但在法律名义上各项重大事务均由知县担负
· 2032 · 台州市志